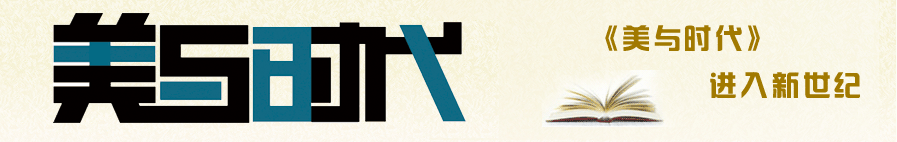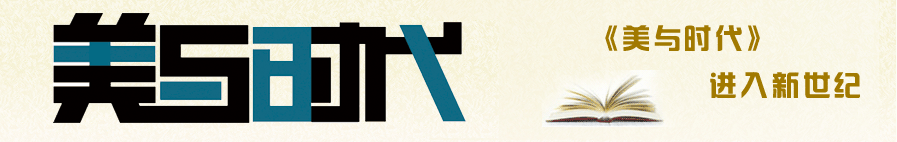立足源流考辨,意图中日对接
——读彭修银先生近作《日本近现代绘画史》
文/王杰泓
日本艺术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彭修银先生的近作《日本近现代绘画史》立足源始,通过对江户时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美术范式转换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考察,客观地还原了一个“后发赶超型”国家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超越与持续性的发展。在中日对接的意义上,日本近现代绘画史的经验和教训或可为中国本土艺术的发展提供某种近缘性的启迪。
作为一个富于“新”、“变”特质的开放性概念,“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是丰富甚至显得芜杂且又变动不居的。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对象,譬如日本近现代绘画史,“现代化”绝对是生动具体而非抽象、空洞的。不仅如此,在亚洲乃至整个东方视阈内,日本的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典型的范本:一方面,作为“后发赶超型”的代表,日本不但在亚洲率先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近代化,而且也是当前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经验”值得世人学习;另一方面,大和民族血液中的“狼性”以及日本社会特殊的运行机理注定了该现代化的“东洋模式”决非完美,其偏失与教训恐怕也是需要引起反思和警醒的。
一
就像对日本这个“搬不走的近邻”始终怀有仇、赞交加的复杂情感一样,在看待日本美术以至整个东瀛文化的问题上,中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矛盾与自大的心态: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及其成就有目共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若言日本文化包括近现代绘画,则又令人生疑,它岂不是中国画之学徒,难道有超越师傅的可能不成?读过彭修银先生的近作《日本近现代绘画史》[1],我们便不难发现上述“常识”与事实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诚然,中华传统文明对日本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日本绘画也一度学习、效法于中国。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究日本为何在艺术文化上有如此突出的成就时,所得却又显得少之又少且似是而非。针对这种略显无知的尴尬状态,《日本近现代绘画史》能够给以很好的解答。事实上,与明治维新对西方科技、政治制度的引鉴相一致,一股强大的艺术变革潮流也在日本国内同步性地展开。例如,刚刚取得政权的明治政府于1873年(明治六年)便受到了在奥利地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的邀请,由此揭开了日本本土美术界与国际官方交流的历史;至于民间传统绘画和“洋画”的碰撞,更是自荷兰登陆日本的16世纪末便开始了(见该书第9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只标页码)。那时,葡萄牙人正登陆中国大明江山,后来又有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宣传西洋油画。不过,与日本相比,中国画与西洋画的真正沟通尚是三百年后维新变法时期的事情。中日之差距,自明治便已经开始。值得玩味的是,近代史上中国画接触西洋画并非直接效法于西方,而是经由近邻日本这个“中间桥”。例如因“百日维新”而创设于1902年的两江师范学堂,其所设的“图画课”就是参照日本学制。“从中国留学生开始到日本计算起,日本留学欧洲的画家已有五代人,其中最权威的是油画家黑田清辉和藤岛武二,我国当代许多留日学生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2]作为向国内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先生于1905年赴日留学研习西洋绘画时,所师从的正是黑田清辉,其后像关良、丁衍庸、阳太阳等人也均留学于日本,并受日本绘画的影响回国后创建了“决澜社”,可见日本近代艺术在自我探索期就已开始发挥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向日本学习的历史。
细究起来,彭著《日本近现代绘画史》的首要特点在考据。如书之开篇就对“美术”、“绘画”、“日本画”、“西洋画”、“东洋画”等根基性概念作出了周详的考辨,其中贯以“考其原始、释其内涵、辨其演变”(罗宗强语)之原则,决不作无“根”之妄议和无依据的推测。具体操作时,作者注重以“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切入对诸概念的厘定。如在历史语义上,“兰画”、“红毛画”、“西画”、“洋画”等皆是日人逐渐认识西方绘画的产物,由此形成“日本画”与“西洋画”、“日本画”与“东洋画”并置的观念和认识;在文化语义上,“美术”、“艺术”等词的引入则彰显着日人对艺术门类划分以及绘画自身哲学认知的自觉,由此迁衍出东、西词汇的“误译”和艺术观念的“对接”问题。这其中,有一段公案值得探究:为什么是“日本画”(而非“东洋画”)与“西洋画”并置呢?彭先生为此补述了一件有趣的事:在1995年的一次“何为日本画”的讨论会上,西方学者就提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没人提出“英国画”或“美国画”,为什么在日本会有“日本画”呢?对此,日本美术史论家佐藤信道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在欧洲,在讲到‘法国绘画’、‘美国绘画’时,是与基本的同一的西洋美术中的其他国家的绘画相比较而言的。可是在日本,在讲到‘日本画’时,没有意识到同一东洋圈的‘韩国画’、‘中国画’,而完全是把‘西洋画’作为对置来设定的。在韩国,讲到‘韩国画’,在中国,讲到‘中国画’时也是这种状况。”(第32页)——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何谓“中国画”:这是本土绘画在面对整个西方文化(他者)时产生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而非单纯的国别意识。这点也符合“日本画”是“一个近代史的新概念”(陈振濂语)的观点。
当然,“日本画”一词的确立也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在纯粹的日本传统绘画和“西洋画”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混合区,如那些直接模仿西洋画而创作的作品,以及各式各样的嫁接西洋画而新成的绘画形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彭先生方未将其敷衍成一部简单的美术编年史,而是立足于该“混合区”的扩大以至主导化,进而提要性地勾勒出日本绘画由传统向现代逐步转型的历程。彭先生认为:“日本的近现代美术并不是与日本传统美术在同一源泉上的区别,也不是在时间上与西方近现代美术有什么关系,而主要是以接受西洋绘画的写实主义精神,以模仿和移植西洋美术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以西方的‘先进’美术来改造日本的传统美术,努力探索使美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途径为标志的。”(第37页)综观该书,近现代日本对西方美术的学习并非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也曾面对着种种问题,例如明治时期美国人芬诺洛萨对日本美术界“盲目西化”的狂热风气的批评,对日本绘画发展的航向起到了很大程度的修正作用。总体来看,自江户时代“日本近代绘画的曙光”初现一直到二战后“日本绘画的现代展开”,中间的时间跨度固然很大,所涉的画家与画派也很多,然而不同时期的主题却是赓续不变的,那就是如何处理“我物”(冈仓天心语)与“他者”、传统与现代之关系。1880年代,日本美术界在怎样处理西方绘画、如何保存民族艺术的问题上形成了四种不同观点:一为纯粹西方论者,二为纯粹日本论者,三为东西方并重论者,四则自然发展论者(第111页)。当时的美术教育家冈仓天心果断选择了第四种,并为历史转折期的日本美术指明了方向。他说,不论东西美术差异,“有理之处便取之,美好之处便研究,根据过去的沿革随着当前的形势发展”,“美术是我们共有的天地,难道还要拘于东西方差异吗?”(第113页)艺术之最终理想,当是“创造一种材料、技法和主题完全日本风格的绘画,这种绘画充分吸取西方写实画风优点,使其具有时代感,又能满足日本传统装饰趣味的审美要求”(第119页)。为此,冈仓天心在自己创办的美术院里开展了“新日本画运动”。这种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基础上的独立的艺术运动,不但给当时的日本画坛注入了新的时代感与自由精神,同时也为日本绘画的现代化找到了审美理想的定位。尽管此后尤其是二战前后,日本新美术运动一度经历过低谷、衰落乃至悲观主义的“日本画灭亡论”,但是自最初纠结于写实主义到后来游刃于现代主义,日本绘画在“东西汇合”路上的步伐已经越来越从容、自在了。——相较之下,我们的“中西融合”之路却走得异常艰辛。以上世纪为例,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用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改良派”,以林风眠为旗手的借西方印象派以来的现代主义革新中国画的“融合派”,以及潘天寿主张“东西方绘画应有各自的高峰”的民族本位主义,三股潮流主导着中国美术近代化的进程。可是直到上世纪末,我们依然还在纠结于中国画是否已经“穷途末路”(李小山语)、中国画是否“笔墨等于零”(吴冠中语)的巨大争议与观念混乱之中,行动上的收效更是微乎其微,这些都暴露出我们在民族艺术的革新上要落后于日本。
二
读彭先生的《日本近现代绘画史》,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浸润的一种强烈的“功利”动机,那就是“日本画”之传统与现代、东洋与西洋之对接,对于“中国画”的现代化或可有某种近缘性的历史启迪。立足现实以解决问题,这是包括中日在内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必然选择,日本近现代绘画史表明,其对于“西洋画”的借鉴起初也是抱着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早在江户时代,“荷兰绘画(西洋绘画)的价值,之所以被当时日本洋风画家所承认,与其说是由于艺术的价值,不如说是由于它的逼真的写实性而带来的实用价值。”(第49页)但是,一定的动机并不足以成为历史判断的唯一依据。到了明治初期,“在美术欣赏方面,随着对西洋美术认识的加深,从注重洋画的实用性,开始向纯艺术的鉴赏性和审美性上转移。”(第63页)由此,日人对于西洋绘画的借鉴开始逐步深入到美学的层面。明治时代以后,日本国内已鲜有对“日本画”概念的争论。大多数日本画家以为,无论是新日本画抑或是日本人创作的洋画,均不过是民族审美理想映照下的线与色,无需另以明晰、一定的界线予以廓清。彭先生显然认同此一观点,早在《中国绘画艺术论》中,他就指出,所谓的“中国画”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其不存在某种共同的本质特征,也没有一个确切、固定的外延[3]。一部《日本近现代绘画史》,读者所见的多非临空高蹈地对画家如何处理个人理想与政治、市场关系的论述,而是以小见大地对绘画点和面的具体展开:在画家、作品方面,从黑田清辉到东山魁夷再到高山辰雄,彭先生为我们呈现的是他们作品中糅合的东西方理念及其对美术界的导向作用;在画派、画会方面,从“四条派”到“物派”、“白马会”到“创画会”,论述的着眼点也是据其对待东西方画法的态度,进而揭示各派的艺术成就和兴衰得失;在画展、院校方面,从东京美术学校到帝国美术院、“日展”,我们虽可看到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然大部分事件的根由仍旧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的态度。通过对西洋画思想资源睿智而大胆的引鉴,日本绘画不但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淘汰,反而为大和文明的自我发现提供了一次次绝佳的契机。
从“日本画”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彭先生敏锐地洞悉到,明治以后“‘书画’向‘绘画’的转换,说明了日本绘画观念由中国转向了西方,由古典转向了近代。”(第17页)至此,中日艺术的差距逐渐拉大。并且,这一转变的另一技术要点在于“明治以降,无论是‘日本画’还是‘洋画’都以色彩为中心。可以说,从此以后近代日本绘画进入了‘色彩化’时代。”(第17页)对于奉“气韵”为圭臬、“赋彩”仅排第三位的中国画来说,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绘画材料的变化,更是绘画技术因素的变化以及艺术准则的变化。这里,我们不禁发问,区别画种的因素仅仅依靠材料和形式么?彭先生的研究显然对此早有准备。“当中国传统文人画这一美学传统传入日本后发生一些变化,即不再固守中国南宗画风,而将北宗的装饰造景等特点带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南北折衷的美学倾向。另外,日本的文人画家也不具有中国文人雅士的闲适消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第55页),而哲学观念和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同样左右着绘画形态的变化。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日本绘画最终形成了自身“和魂洋才”的状貌。
返观我们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西方绘画在16世纪末即已东渐于华夏,但是,直到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时期,西方美术才被国人严肃地对待。在此之前,西画都是作为“蛮夷之物”或营利的手段而被接受的,甚至往往被直斥为“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邹一桂语)。那时,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无不认为油画虽拟物逼真但是韵味全无。中国画重笔墨,而日本画重装饰,加之日本向属“文化输入型”国家,其“传统文化具有较成熟的内部反应机制”,因此在对待外来物种包括油画技法的问题上,日人远没有中国人那么强烈的优越感与排他感。“百日维新”之时,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国人遂对日本的崛起感到震惊,于是出现了留日高峰。通过日本这一“中间人”,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美术的理念、技法包括术语。“五四”之后,赴法国留学学习绘画亦蔚然成风,国人又进一步直接学习西方美术,甚至跟上了当时的现代主义潮流。这一时期,中国画出现新变,各种新的绘画形式开始产生,中国亦由此迈出了美术现代化的第一步。其中,握有政治话语权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宋代的写实绘画是近乎科学的艺术,而后来的文人画则是对这种科学精神的摧残。梁启超因此提出“科学化的美术”概念,大力赞誉西洋画和宋代的花鸟、人物画。在“中西汇合”思想的鼓吹下,当时的“现代艺术运动”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相当热闹。当然,运动中也伴随着强烈的派别纷争,如带有巴黎之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派,再就是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派等等。在一个“救亡大于启蒙”(李泽厚语)的时代里,徐悲鸿的主张自然占了上风。他反对现代派的“为艺术而艺术”,同时也反对艺术的功利心,唯一不反对的是艺术一定要“干预社会”。徐悲鸿创作勤奋,勇于表现,作品通俗而深入人心,其赤子之心和领袖之气引领了当时美术界的潮流,并在后来契合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除他之外,那时的中国新美术还诞生了诸如齐白石、李叔同、丰子恺、潘天寿、林风眠等一颗颗的巨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突出者如林风眠),也如冈仓天心般坚持本土艺术的“自然发展论”,主张中西融合,并且有意识地将西方美术的理念、技法自觉融入到各自的绘画实践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一直遭受冷遇的国画重新获得生机。与此同时,在普遍执行国家“普及性、通俗性、革命性、主题性、写实性”[4]的大方针下,西方的新潮美术运动被挡在国门之外,中西融合之路被阻断,代之而起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模仿与学习。1950—1970的三十年间,中国美术处于“现实主义一体化”的理念之下,特别是“文革”十年,更处于“三突出”原则的严格限制当中。而此时的日本则已实现了独自的现代美术创新运动,并且已经能与西方现代艺术分庭抗礼、互相影响。——检讨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运行轨迹一直伴随着政治对艺术的浸淫与主宰,这种情况在日本近现代绘画史上恐怕只有昭和初期的无产阶级美术运动方可以比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始终和“国难”相伴随,美术家总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亡情结,并且时不时还散发出过分的政治火药味,唯美的读者多不易从中觅得一份轻松、淡雅的谐趣。
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面对日本的后发赶超、后来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落后得太多。无疑,日本力图使自身传统艺术向全球化转型的努力是成功的,他们更清楚要保存“本土性”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全球化”。在特定的历史际遇和空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日本并不是只抓住了“西洋画”这根救命稻草,而是在深度与广度上回归活生生的现实,深入探究二战以后令国民生活失去的“从容”与“宽裕”的根本动因。有了这种“问题意识”,日本现代艺术的“日本特色”方具有可能。与之相对,中国则是大跃进式地将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异质性的现代艺术理念简单地并置、糅合,尤其忽视民族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自身的艺术史逻辑。问题意识与文化针对性的缺失,窃以为是阻碍中国本土艺术现代化的瓶颈之所在。
站在中日对接的立场上来看,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同属“东洋”,并且曾经相互影响,两者的绘画艺术无疑具有极强的东方性与近缘性。日本当初之所以没有选择“东洋”的概念,当然还受到“脱亚论”的影响,企图让日本绘画独据种族艺术的鳌头,后来他们做到了。与之相对照,中国人从不愿接受“东洋”的原因,一者它是一个充满殖民腥臭的字眼,二则也不愿意让日本这个学徒与自己平起平坐。但是,直到今天,在经济、政治、文化包括艺术等各个层面,中国人是否已经或者即将重拾到那份可贵的自信?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彭著《日本近现代绘画史》以民族艺术与外来艺术的融合为脉络,真切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后发赶超型”国家如何实现艺术文化的自我超越与持续性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则启示,更是预言……
三
一谈到“史”,我们的脑海中可能立即会浮现大部头的著作。作为一本艺术史著作,彭著的体量或许并不“丰厚”,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却颇为“深重”。近代史的写作不同于古代史,后者面临的难题多是缺乏充分、有效的史料为佐证,而近现代的共时性则让我们难以站在后来的角度、以当代的视域来明辨艺术史的上下文,因此它往往显得不够远视和客观。这就好比拿着放大镜看长城,其结果很容易成为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所以,在近现代美术史的写作中保持价值判断的独立性以及宏阔的历史视野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点上,彭著丝毫不作人云亦云之论。例如,在论“官学派”与“在野派”的问题上,彭先生明确指出:“白马会与太平洋画会的对立,在日本近代美术史上通常被认为是官学派与在野派的对立。从世界美术史的史实来看,这种划分显然是有问题的。……”(第167页)
艺术史的著者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编排者”,一种是“写作者”。传统意义的史学研究应该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也就是艺术史的“编排者”,显然,彭先生属于后者。大卫·卡里尔在《艺术史写作原理》中曾经指出:“一个好的阐释必须忠于事实,言之成理并具有独创性。写这样的艺术史的阐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为孤立的事实不会告诉艺术写作者如何编排她的叙述。”[5]《日本近现代绘画史》一书正包含着彭先生史学研究的个人独创性,而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罗列。这种个人因素的介入不但不意味着主观随意性或者论断的不公正,恰恰相反,宏阔的知识视野和巨细无遗的实证研究为我们解读日本近现代绘画史提供了多种新的角度和可能。著作开篇,作者便高屋建瓴地指出,“但绘画史又绝不等于一堆散乱的材料(绘画作品)的总和,而是由以特定方式发生于特定时间、地点的事件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构成的。”(第1页)又如第四章谈到明治美术的指导者冈仓天心时,著者从“鉴画会的讲演”、“日本美术史”、“黑格尔艺术哲学”等多个角度全面解析了冈仓的美术教育思想和史学观,同时还审慎地阐释了其与芬诺洛萨的关系,进而扩展到冈仓的艺术理想与日本绘画对“第三条道路”的探寻。通过这种多元化的视角和系统化的分析,著者在纷繁芜杂的历史中抽丝剥茧般地提取出一条主线,从而还原了一个极立体的美术史情景。此种功力非一日可以达致。
另一方面,美术史写作的维度也是考量特定著作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日本近现代绘画史》历时性地梳理了日本绘画自身的发展流变,同时又共时性地比较了不同画种以及“日本画”所受到的来自社会、经济以及哲学等方面的影响。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双重考察,著者不完全从作品和艺术家着眼来构建美术史,而是颇具历史眼光地考虑到了美术史家、美术批评家对艺术史进程的影响。书中既包含了对绘画本身的具体探讨,也囊括了对特定时代语境的还原性叙述。
笔者向来主张“以小见大”、“以艺观道”。这里的“艺”可以是具体的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同样也可以是艺术史家和有关艺术史的著作。窃以为,一部好的艺术史著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解读艺术作品、体味艺术家的思考,其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件好的艺术品。而艺术史著作之所以能成为艺术作品,前提在“真”,即关键在于它独特的写作方式和个性化的价值蕴含。从这个角度衡量《日本近现代绘画史》,它同时也是一件值得反复回味的艺术品,因为我们既可从中读“史”赏“艺”,也可以澄“怀”味“道”。
注释:
[1]彭修银.日本近现代绘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5页
[3]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9页
[4]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5页
[5][美]大卫·卡里尔.艺术史写作原理.吴啸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页
作者简介:王杰泓,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编辑:豫 民 |